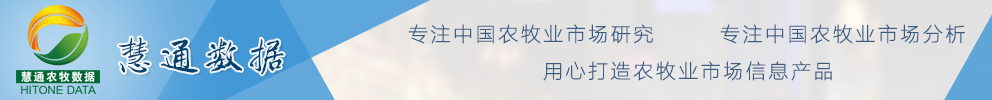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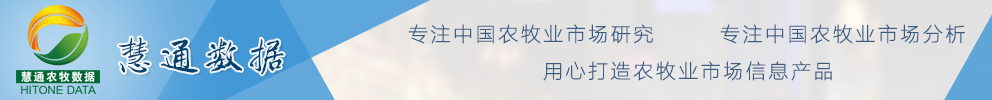
慧通综合报道:
一,重建故乡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树老墙颓。”此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忧虑远在农村的故乡。
中科院地理所3月26日发布 《中国乡村发展研究报告——农村空心化及其整治策略》说,农村“空心化”非常严重。
延续了几千年的乡土生机在现代中国日趋黯然。青年男女少了,散步的猪牛羊鸡少了,新树苗少了,学校里的欢笑声少了——很多乡村,已经没有多少新生的鲜活的事物,大可以用“荒凉衰败”来形容。
与此同时,乡村的伦理秩序也在发生异化。传统的信任关系正被不公和不法所瓦解,勤俭持家的观念被短视的消费文化所刺激,人与人的关系正在变得紧张而缺乏温情。
故乡的沦陷,加剧了中国人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也加剧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的秩序混乱。
滚滚向前的城市化步伐,不能继续以牺牲乡村的土地、德性、风俗、传说等以及家族观念为代价。
此时,有一些中国人,开始用行动,重建故乡的伦理、信任,以及生活方式。可以说,各种新的“乡村实验”在不声不响间进行。
80多年前,诗人闻一多的一首诗,可谓这些“故乡”重建者的心声。
“什么是家乡?它代表着一种安全感,你知道楼下的餐厅不会给你吃地沟油;它是一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地方。”怀着对故乡的一种信念,郭中一放下一切回到故乡开办农庄、书院,不是隐居,甚至不是叶落归根,而是“践行”。
郭中一永远是一头乱发,向后飘散,突出亮堂堂的大脑门。无论是什么话题,他都是微笑着,用浓重的台湾口音徐徐道来,个中却不时夹杂着老顽童一样的尖刻。
我们从他的故乡谈起,谈合肥市肥西县南分路口乡,现在叫铭传乡。身为台湾的大学教授,他却放下一切回到大陆的故乡开办农庄、书院。不是隐居,甚至不是叶落归根,而是“践行”。郭中一说,这种理念在哪里都可以实现。所谓故乡,只是一个载体。
二,归人
郭中一:父亲一生保留着肥西口音,发不出“xi”这个音。“水烧好了,你先洗还是我先洗?”就成了“你先死还是我先死?”从小我填籍贯,都要写安徽合肥。所以我一直知道,我是合肥肥西人。但合肥是什么样子的,我不知道。”
2004年,故乡第一次呈现在郭中一的面前。
彼时,合肥的市区还很小,城市化和工业开发区的脚步尚未迈开大步往前狂奔,让人目眩神迷。彼时,郭中一还是台湾东海大学物理系副教授、美国毕业的物理学博士。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台湾合肥同乡会新任会长。身为会长,却从未见过故乡,总是有些尴尬。于是郭中一赶紧找机会回来看看。
故乡和郭中一离去时没有什么两样。农田嵌在荒山中。杂树、野草、荆棘,不要说能行车的路,人能走的路也很少。故乡的姑姑说,幼时她曾在山上遇到野狼,心里狂跳,只敢慢慢后退几十米,然后发足狂奔。几十年后,郭中一沿着同样的小径上山勘查,狼是没有了,却能看到野猪的蹄印。荒景中,“山大王”“人肉包子”这种章回小说里的词竟会跳入郭中一的脑中。回到乡政府时,已是一片漆黑,没有一点灯光。郭中一说,那大概是他出生以来看到过的最黑的夜景。
乡长说,真是抱歉,这里还是很落后。教授却回答道,第一,这是我的家乡,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第二,你觉得这是一种缺憾,但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长处。台湾已经找不到可以看星星的地方,就看你怎么规划了。
彼时,台湾已在流传“萤火虫妈妈”的故事。一个妈妈给孩子解释成语“囊萤映雪”,孩子却不知道什么是萤火虫。妈妈突然想起,台湾似乎已经没有萤火虫了,便去问昆虫学家,这是怎么回事儿?学者说,你要有干净的草,要有干净的水,要有没有光污染的天空。于是,这个社区的妈妈们联合在一起,执行以下规定:本区不准再用除草剂;废水不能乱排,基础设施为此而改造;所有路灯全部改装为暗色,紧贴地面不高过膝盖;机动车进入小区必须关灯萤火虫就真的到这个小区来了。原来,萤火虫是个环境指标,台湾很多地方都开始做萤火虫繁育。
第一次回乡之行,只是生态农庄的伏笔。2004年,郭中一的人生舞台还在台湾,只是想不到,场景竟会日渐逼仄。这一年,民进党竞选时,竟号召“把外省人都赶到海里去”。“去中国化”已成为台湾的高分贝话语,甚至连名片上的“合肥同乡会会长”,也成了一个问题。郭中一等外省籍知识分子们常感慨,干吗要受这种屈辱呢?
同侪聚在一起,就不禁聊起将来。“中央大学”的李河清教授曾说:“很多老师都在做一个梦。因为对现有居住环境不满,就想去山里找一块地,做自己的社区。我们能不能为自己设计一个无污染的社区?然后,在这个社区里创造一个好的文化氛围?”这一倡议很快成为小圈子的共识。
这群所谓的“外省籍”知识分子中,只有郭中一和自己的省籍有真正的联系。于是,十几位博士、教授合资,由郭中一夫妇牵头,确定在肥西建设生态农庄,完成晚年的田园梦想。
三,荒山
庄蕙英: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生态农业是要扎根的,不会让你一夜致富,要从基础开始,慢慢来。但产生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有科学分析说,地球上多一座生态农庄,世界上也就多一个百岁老人。真正做下来,才知道难度有多大。
郭中一的夫人庄蕙英是生态农庄真正的奠基人。2006年夏天,庄女士带着两个儿子在合肥开始建设。此时,郭中一正在台湾忙于组织“反军购大联盟”的社会运动,直到2009年,终于辞去教职扎根于合肥。
郭氏夫妇在肥西看过很多地方,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放弃。庄园坐落的小团山,在那时只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连地方官都不建议在此开建庄园。但是庄蕙英坚持租下,“地无不可用。人人以为是荒地,弃之不用,岂不可惜?”
但原始条件的恶劣,不得不花费大量资源去弥平。因为是荒山,表面的土层非常之薄。庄蕙英记得,最厚的地方仅25公分,不过两本辞典那么厚,几乎不可能种树。于是,为了填土,不得不在山脚下取土,向上填埋,卡车来来回回1000多趟,才夯出一个农业的基础来。
荒山里,常会挖到无主的孤坟。庄蕙英说,前后一共挖出47座。每挖一座,就按照当地人的习俗,放一串鞭炮,移葬到统一的地方。在水、电未通的时候,郭夫人经常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荒山里,伴着孤坟过夜。
一开始,郭氏夫妇的设想是养一大群鸡,在山上养肥再拿到城市去卖。要养鸡,就要盖房子。于是有了第一栋建筑,就是现在农庄的活动中心。因为是生态农庄,杀虫剂和农药是违反原则的。结果到了夏天,窗口扑满了嗷嗷待哺状的蚊虫,让人发愁。怎么办?有人提议种薄荷试试。果然,在房子周围种上各种香草之后,清香弥漫,蚊虫大减。郭氏夫妇再试着把香草种到蔬菜和果树边上,也防止了虫害。本来只是防虫用的香草,也到了收获季节,能否利用呢?喝茶是一种。不过,饮用的消耗量远没有这么大,郭氏夫妇又琢磨着做香包,提炼精油不过几年,迷迭香、罗勒、薰衣草等已是生态农庄的经济支柱。小团山正式定名为“香草农庄”。
“产业链根本不是一开始规划的那样,其实有点歪打正着。我们只是一个在有机农业的想法下,慢慢推进到现在。” 庄蕙英说,“所以,我们也不知道生态农庄的将来,会是什么样,顺其自然吧。”
小团山的土质为氧化铁,呈褐红色。就肥力而言,非常贫瘠。但郭教授夫妇坚持“生态”的理念,不准用化肥和杀虫剂,哪怕一年没有收成也在所不惜。因此,肥力的改善,只能通过物种的栽种,和天然肥料慢慢推进——就像一个先天不足的婴儿,后天调养就格外重要。四年后,这一工作只是初见成效。
郭中一说,生态农庄的特点,就是早期投入大,收获往往在十年以上,但功效,是重建生态系统。他不喜欢“有机农产品”的标签。因为当下的有机食品生产,在他看来,大都是以工业化的方式,进行大面积、机械化、流水线作业,收获的是单一农产品。这种方式,对日渐凋零的农村,几无裨益,连就业的增加都很有限。而所谓“生态系统”,是在农庄里建立丰富的物种群。所以,产出和播种轮换出现,农庄几乎没有“农忙”和“农闲”之分。
时至今日,生态系统已初见成效。原来只有荆棘的小团山上,光是鸟就有25种,种下去的植物,更是百种以上。起初取土挖的大坑,积累雨水成塘,没有人管过它们,却不知怎么就有了鱼虾螃蟹来安家。
在这个生态系统中,重构的不仅仅是生物的多样性,也包括人和自然的关系。
山庄里曾养过一只兔子,每天到山里面瞎玩,晚上才回来吃东西,睡觉。有一次,所有人都在电脑前忙,兔子却来蹭蹭这个人的腿,磨磨那个人的鞋子,希望有人关心它,陪它玩。但没人有空搭理它。兔子一怒之下咬断了办公室的电线,然后就像做了错事的小孩一样,缩在角落里一动不动,眼睛都不抬一下。
有一天兔子突然不见了。大家都怀疑,它是不是找到了自己的同伴,回大自然去了。这样也好,它有了自己的天地,当然比在人群里孤零零地生活要好。但过了两周,它回来了,很快又走,这次大家都有了心理准备。果然,它再也没回山庄。
又过了很久,一天下午,郭中一和次子延极在桑葚树下散步,突然听到很远的地方,有唰唰的声音,疾速贴着地面传来。不是人的脚步声,也不是风声。是那只兔子,从林子里跑出来,到了离人大约一尺的地方停住。人走上去想再摸摸它,它却拒绝,退到相同距离之外。人向前走,它就依着人的速度,默默跟上。就这样,若即若离地走了一个多小时,它才再次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