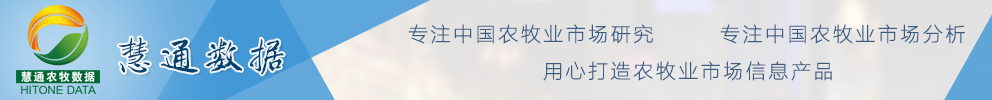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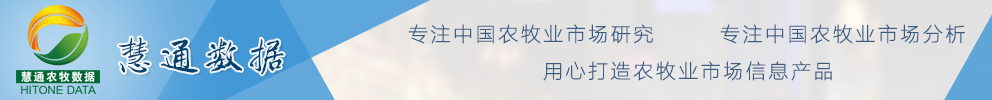
慧通综合报道:
说到中国的粮食安全之道不在于减少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依存度,而是如何在进一步提升自身粮食生产效率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我们自身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有朋友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不能太指望国际市场,因为中国体量太大,买什么,什么就涨,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全球农产品市场供需平衡和价格稳定的破坏者。长此以往,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也会因为农产品价格上涨对劳苦大众的损害而遭破坏。
这种农产品领域的“中国威胁论”不是特别新鲜的论述,之前也在诸如石油和铁矿石领域轮番出现过。国际人士的紧张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中国的“进场”必然会打破原有的稳定与平衡,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全方位看待全球市场中的中国买家效应。事实上,正是中国对大宗商品的购买力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非洲和拉美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全球化的深化必然会不断将新的玩家卷入场内,原有的平衡也就屡屡会被打破,但人们总会借助市场的力量找到新的平衡点,石油市场的跌宕起伏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全球化这盘大棋,没有永远的赢家,也没有永远的输家,关键是如何在竞争中趋利避害。除非我们放弃全球化,回到自给自足的年代,否则这场赛局无可回避。当然人们可以通过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减轻市场的震荡及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但从一个平衡走向另一个平衡将是永恒的主题。
还有的朋友认为打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必然会陷中国农民于不利的境地,因为在包产到户解决了“苏联命题”中积极性不足的问题后,囿于小农经济的碎片化效应,中国的农业生产效率很难再大幅提高,所以中国小农很难与国际生产者相竞争。
小农的低效的确曾一再被历史所证明。由赫德等人主持的清帝国海关在分析19世纪80年代中国茶叶为何不敌来自斯里兰卡和大吉岭的竞争时指出,与这个地方的规模化经营的茶叶种植园相比,中国的茶叶“来自零星的种植在角落的灌木上,由数百万独立农民生产,并被带到被数千个在不同地区经营的独立代理商搅得杂乱无章的市场上”。
这一局面还因小自耕农抗风险能力的低下而更显恶化——农民家庭首先要保护其生存需要,然后才参与市场。事实上,水稻和某些农作物在最活跃地参与世界市场的种茶地区仍一直被栽培,当茶叶行情出现阶段性大规模下调时,茶农们毫不犹豫地毁掉茶园转种水稻。如清帝国海关总结的那样,“必须记住,中国的茶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仍是一种农业副产品。”
茶叶案例可以说充分凸显了中国“三农”问题的历史悠久性:农村人地矛盾突出、农业产出效率低下、农民生活改善无望。如今,“三农”问题再次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块短板。突飞猛进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相比,更加凸显了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相对滞后。
一方面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农产品的供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对土地的需求,客观上又加剧了中国可耕地偏少这一自然禀赋的不足。此外,工业化本身对来自农产品的原料的需求,比如以玉米为原料的乙醇汽油的生产等,也加剧了农产品供给的刚性。
也因此,在人们几乎忘记当年的“四化”口号之时,近年来高层再次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口号,并将其提到和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并列的高度,冀图以新“三化”化解老“三农”。
当然,考虑到中国农村人口规模的巨大,以及由此带来的非农化所需的较漫长的时间成本,坐等规模经营条件成熟再推进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显然是不适宜的。如何通过中间的加工、流通和销售环节的组织化和市场化,即纵向的一体化来有效对接在长时段内比如“顽固”存在的小农户经营单位,是更需要各方戮力求解的问题。在这方面,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资本和劳动力双密集的农户经营模式,比美国的大农场模式,对于中国大陆地区的农业现代化而言显然更有借鉴意义。
因此,判断小农户经营是否一定有悖于现代化,或者说一定阻碍农业产业化的实现,关键是看其如何通过自组织能力的提高,通过“社会结构”的变革来有效对接市场。在其《农民的终结》一书中,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展现了法国农民是如何完成这“惊险的一跃”的。
在孟德拉斯看来,那些沉迷于“个人主义”和“土地恋”的法国农民一度曾怀有这样的梦想:在吸收了一些新技术和接受了一些经济制约之后,也即一旦适应期的危机过去之后,他们可以重新创立一种能够和以前一样持久的耕作与经营的体制,进而重新找到类似他们父辈熟悉的那种平衡。
然而技术文明有着自己的节拍。像其他生产领域一样,农业也必须服从工业社会中技术和工业变化的节奏。一切农业生产都受消费者的欲望和市场的变化所支配。农民不仅远未重新找到传统的稳定,而且将经受技术革新和经济趋势带来的长期变动。开弓没有回头箭,为了应对这一长期变动,法国农民或主动或被动地走上了农业现代化和经营集中化的道路,从而“被卷入”了一场自改变“技术结构”始、至变革“社会结构”终的历史性事业。
在孟德拉斯看来,法国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具有惊人的适应性,一旦对经济的前途和“乡村职业的高尚”重新确立信心,他们可以按照工业社会的经济规则行事,利用邻居外流的时机扩展自身,并以“惊人的可靠直觉去创立一些全新的和非常符合现代要求的机构(农业技术研究中心、农业集体利益协会、家庭乡村培训所等等)”。
在这里,不难看出,“邻居外流”和农民的“自组织”是“终结”小农户的两个关键前提,前者是农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后者是对接技术与市场变化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尽快结束对农民工进城的“欲迎还拒”,同时尽快放开对农民自我组织的限制,是顺遂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不可或缺的前提。
文章来源:慧通农牧信息资讯转载于华夏时报,欢迎垂询交流!